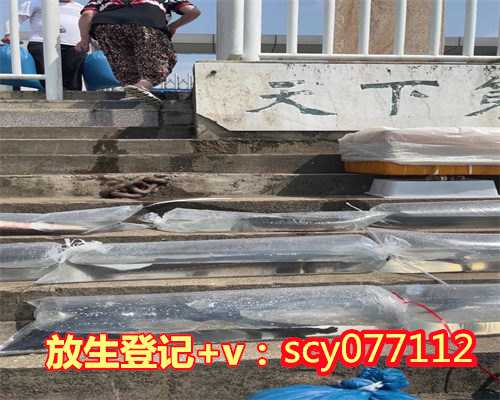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之探微——关于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间净土思想发展的一些思考
云南放生流程项运良
世俗化是现代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现代中国佛教也在经历这个过程,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间净土思想的产生、发展是其突出表现。本文以太虚、印顺和星云三位佛教思想家和实践家为代表,着重探讨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历程、趋势,阐述各思想体系之间的异同,指出他们共同点是将净化社会、人的精神满足及物质帮助放在第一位,建立以人为本、适应现代社会、提升现代社会的佛教理念。这也表明了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过程与现代化过程并行不悖,世俗化,意味着现代中国佛教更多地关注人及人类社会,也就意味着现代化,这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要求。
一、世俗化含义
世,即一个时代,有时特指三十年;俗,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世俗,意指尘世的、非宗教的。这意味着社会上流行的是所谓平凡的,而与之相对的宗教领域则具有神圣性。
武汉放生方法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的概念,关于世俗化的概念,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一般来说,主要是用来形容宗教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褪去宗教色彩,宗教与社会其他领域相分离,由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从而引起的对其他领域影响的减弱或控制程度的弱化。
鳝鱼放生放到哪里合适
可以这样理解,“世俗化”即“非神圣化”,意指宗教传统神圣观念和象征的退隐,人们对宗教的神圣感、神秘感被今日之理性与现实取代。“非神圣化”之后,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在思想、行为、组织、场所上体现着与世俗的极大不同,但宗教本身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同时,“世俗化”也意味着宗教在积极回归现实世界、直面现世人生,强调对现实的关切和自身的现实作为,在任何时候,神圣化与世俗化都并行不悖。这样,宗教并未被“世俗化”所湮灭,而是促使宗教更全面、更广泛地渗入现实生活,在社会存在及发展的方方面面以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潜在的方式顽强地体现其自我,为社会作出其积极的贡献。
所以,世俗化是宗教逐渐丧失以往在世俗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回归神圣自我而又相对局限的领域,通过反哺世俗社会,专注于民生问题,体现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发展方式,从而通过世俗化实现现代化。
二、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
所谓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是指:人们对佛教的宗教神圣感、神秘感的消解,佛教神圣地位的逐步弱化;但佛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依然深刻地影响世俗生活,佛教呈现出积极回归现实世界、直面现世人生的趋势,重视自身现实作为,全面广泛地参与现实生活,专注于民生问题的解决。
佛教所关注的中心是“人”,是现实的人生。“人”是佛教产生、存在、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佛教一切问题的中心,没有人便没有佛教。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自始至终便是关于“人”的宗教。
(一)“人生佛教”思想是中国现代佛教世俗化的开端
人生佛教是由太虚大师于20世纪初提出的宗教理念。当时佛教发展出现了内外交困的情况,就内部来说:一是佛教给人第一印象总是消极隐遁,清心戒欲,出离苦行,远离人间,独善其身;二是一说到佛教就给人以神秘感,呈现于人们视野的总是念咒、焚香、敲木鱼、超度等,带有迷信色彩,甚至与之等同。此时之佛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其义理、哲学思想的发展几乎停滞,对现实的关注也随之放松,渐渐远离人生,成为巫鬼教、神教。其次,就外部来说,现代之初的中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加之无神论的快速传播,迫于生计,社会上经常出现驱僧夺财、毁坏寺庙佛像、占庙办学的现象。
对此内外交困之情形,太虚大师针对当时佛教某些不符合社会需求的现状,以及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在致力于整理僧伽制度实践的同时,为展现佛法对人生的真义,努力回溯佛法本源,以寻求推进佛教革新的根本性依据,促进佛教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佛教革命三大主张”。
我对于佛教协进会所定的章程及宣言,虽极和平,然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当时的《佛学从报》曾加反对。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1]
由此可见,太虚大师之所以提倡佛教改革,就是由于当时佛教自身专事于人死后天堂说教,缺乏对现生的应有关注,躲在神秘之暗处,让大众无法沐浴佛法之灵光。因而,太虚大师强调佛教要“涤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于各个时代背景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的圆渐的大乘佛学’”。“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修学菩萨胜行,“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也就是要打破佛教被误认为的神秘而又神圣的灵光圈,将佛教等同于纯粹的精神生活,认为佛教回避现实生活的错误看法。
锦鲤鱼放生河里后能活吗
恰恰相反,佛教立教之本意为拔苦与乐,是要让人直面生死这个人类的根本问题,让活着的人在现实中摆脱“八苦”,排除现实中的万难,积极生活,行善积德,做一切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事;让即将入木之人摒除对死的恐惧,给灵魂以人性的关怀,从而使人断灭生死观念,达到极乐。因此,佛教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不能躲在一处独善其身。“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才是佛教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人类达到理想生活与境界的手段和载体。所以,太虚大师推行改革是因为佛教的世俗化,即在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减弱;太虚大师强调的人生佛教,其本身也是一种世俗化,就是要让佛教进一步与世俗生活接轨,鬼事与人事并重,为世俗社会实实在在地做一番事业,达到扎根于民和影响重建。
可以说,人生佛教理念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意味着现代佛教世俗化进程的开端。
(二)“人间佛教”思想推动了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进程
“人生佛教”,是太虚大师针对重鬼神的中国佛教而提出的,“人间佛教”则是印顺法师以佛教的天化、神化情况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去除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深深地植根于人间。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是现代佛教世俗化的深入发展。
“人间佛教”是人生佛教的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印顺法师(1906-2005),是当代台湾佛学大师,太虚大师的学生,“人生佛教”理论的坚决拥护者。20世纪40年代末,印顺大师进入台湾后,一直以弘扬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论为己任,继承和发展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印顺法师常说,他提倡的是‘人间佛教’,但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也说,他提倡的是‘人间佛教’。可是,坦白说,两者的内涵并不一致,而且‘人间佛教’一词,仍是印顺法师为了修正太虚的‘人生佛教’而提出来的。其酝酿此说的思想背景,是为了减低‘人天乘’中的‘神通色彩’,而合于《阿含经》中‘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的说法”。[2]因而印顺法师所倡之人间佛教乃为去除佛教中过于神通之色彩,回到现实人间,把人、人间作为改造的对象。
印顺法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一文中说:“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现在不过将他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抽绎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佛是我们所趋向的目标;学佛,要从学菩萨行开始。菩萨道修学圆满了,即是成佛。”[3]菩萨行的特点是普渡众生,依戒以成佛,施爱于众生,拔除众生之苦,将爱播撒于世间,这意味着“人间佛教”是要在现实世界追求悟道成佛,将人在现实中的广行善事作为成佛的重要标准,即现世菩萨行是成佛的关键。说到底就是要求广大民众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生活和各种公益事业,而不单是精神的跃升。相反,那些所谓的精神神通、善于鬼事会有碍于佛教的发展。
因此,“大师说‘人生佛教’,我说‘人间佛教’。一般专重死与鬼,太虚特提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法以人为本,也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4]这意味着印顺大师继承和发展了太虚的佛教思想,要求佛教徒不偏于神化佛教,而应专注于世俗事务与民生,践修菩萨行,以此达到成佛。他认为:“所以特提‘人间’二字来对治他:这不但对治了偏于死亡与鬼,同时也对治了偏于神与永生。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惟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人间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佛教不能只关注人生问题,也不能将佛教神化、天化,佛教更应参与到人间、社会中去,努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是因为佛教偏出世俗生活,过于将佛教神化、天化,与佛教本意相左,这使得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减弱,有丢失群众精神领地的趋势,无论对于民众,还是佛教自身都是相当不利的,他试图由关注个体的人转变到关注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而这正是现代佛教世俗化的有力表现,即便是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也是要佛教更好地融入世俗生活,推动了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进程。
(三)“人间净土”思想是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的高峰
随着世俗文明的发展和贫富分化的加大,世俗社会呈现出极不和谐的状态,部分人可以凭借金钱和财富坐享其成,人的生存空间和人本身都面临着挤压和掠夺,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虚浮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尊严难以得到体现和保障,甚至民族文化、国家、价值体系也可能在强权的摧残下崩溃;同时,由于人类盲目的改造世界,自然环境和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地球难承载起无限制的欲望。在一定意义上,世俗社会的自然、政治、人文、科技……不能为人提供一个符合于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使得“人间净土”思想应运而生。
净土即:菩提修成之清净处所,佛居之所,无五浊之垢染。人间净土即是将人生之社会转变为清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一方面表明世俗社会有许多令人不悦、不利于人类发展的地方,另一方面是说可以通过倡导佛教将净土建在人间,实现和谐而极乐的社会秩序,转娑婆为极乐,化人间为净土,人间即净土。
人间净土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星云法师,其在一九九O年元旦《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的演讲中指出求佛成佛、往生净土不一定要到来世,佛教不仅要让人往生极乐,还要让人生活于现世净土,即在人间建立净土。
我们人人要有一个目标,追求往生净土,在西方有极乐净土,在东方有琉璃净土。其实净土不一定在东方、在西方,佛教的净土到处都是。弥勒菩萨有兜率净土,维摩居士有唯心净土,我们大众说人间净土。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人间创造成安和乐利的净土,而要寄托未来的净土?为何不落实于现实国土身心的净化,而要去追求不可知的未来呢?[5]
星云法师也是人间净土思想的践行者,其开创的佛光山事业蒸蒸日上,成为实践人间净土理念的强大载体,佛光山事业的道场、慈善及文化教育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修建了养老院、学校、医院等,化度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精神信仰层面的需求,还给人们提供物质帮助。“在我们本山对于具有某种护教程度的信徒,老年的时候,由本山为他颐养天年,不一定要儿女来养他,甚至也不一定要到往生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让阿弥陀佛来补偿他,对他说:‘你对佛教很好,我来养你,给你往生。’以佛光山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寺庙道场,要给予信徒的信念──我这里就是西方净土,我就能给你安养”。因而在星云法师看来,人间净土思想“是入世重于出世的,生活重于生死的,利他重于自利的,普济重于独修的”。这就说明:人间净土思想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实践和修行将人间改造成人人各得其所、和谐共存,人人心怀社稷、他人的理想社会,将净土带到人间,不仅关注人间、人生,还要使佛教思想起到净化社会的作用,在人间建立净土,而不是专注于往生与独修。
由此看来,人间净土思想第一次将彼岸的净土极乐世界带到现实的人间,这一点与某些社会思潮殊途同归,即是将理想的社会模式应用到现实世界,希望在人间创造一个人人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大同社会。可以说人间净土思想是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也是佛教思想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不同于以往佛教思想只重往生净土世界的精神追求,而不重视宗教理想实践的观念。而这一点也恰恰证明了佛教的世俗化,佛教在由以精神解脱的彼岸世界为重点转身以人间宗教实践为重点,佛教认识到:任何一种宗教只有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健康地发展下去,只有为群众提供相应的精神满足与物质帮助,其理论才能更好地深入人心,更多地争取信徒,普及其价值观念。因而,由彼岸到此岸,由独修到实践的过程,就是佛教植根于群众,从最基本的世俗生活做起,服务于群众,不断扩大影响、实现牢固立位的世俗化过程。
“人生佛教”思想反对佛教专注于鬼事、神事,要求鬼事与世事并重,积极融入世俗世界,重视人生;“人间佛教”思想要求在现世中淡化鬼神之事,不应将佛教天化、神化,而应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世俗生活上,在世俗中给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和物质帮助,倾向于人间、社会;人间净土思想则希望在世俗社会中建立起极乐净土,或者说佛教的使命就是将净土带到人间,不仅关注人生、人间,还要注重实践将净土带到现实社会。可以说,现代中国佛教的三种发展形式均是紧密围绕“人”来进行的,反映出佛教领袖对于佛教淡出世俗社会各个领域的忧虑,力图通过积极入世的方式重建佛教影响的愿望,对于提高佛教的影响力、促进佛教的传播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满足了一些群体的需求,对于净化社会起了积极作用,推动了社会进步。
但这三种形式终究是现代佛教发展的三个阶段,三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其积极入世的愿望逐渐增强,佛教的地位和影响也一步步提高,由鬼事与世事并重、淡化鬼神之事到建立人间净土,由人、社会到极乐净土,将彼岸极乐带到现世此岸,是一个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现代佛教世俗化加快的影响,佛教以更快的速度退出原来极大说服力的领域,需要重建其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世俗化的同时,佛教开始更加现代化,以独具特色而又适合自身及众生需要的形式发展,近几年佛教捐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参加抗震救灾等活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世俗化促进了现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
总的来说,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间净土这三种形式均可归入人间佛教的范畴,无论太虚大师、印顺大师,还是星云大师,其思想的核心都是佛教度“人”,按照佛教的要求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式,将净化社会、人的精神满足及物质帮助放在第一位,建立以人为本的适应现代社会、提升现代社会的佛教理念。但人的这种需求与满足不是无限制、无约束的,其标准应是佛教基本义理。
就笔者看来,这三种形式确实促进了佛教的现代化,使佛教影响力得到提高。但这恰恰也是现代佛教世俗化的表现,这种趋势必将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在现有科技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宗教实践性的功能被科技发展所证伪,宗教神秘性受到了极大挑战,佛教的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佛教要避开这种直接冲突不得不改变其发展形式;同时,对人的本质的寻根问底是人类的本能,而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异化”严重,人类对于自身前途感到茫然,对于世界性问题普遍感到担忧,对于明天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呈现出迷茫、恐慌和无所适从,并伴随着大量的自杀、自虐倾向,人们内心开始丧失应有的道德准则,道德底线被不断突破,这些问题的出现为佛教精神性满足提供了土壤。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具有普世性,其出发点是解决人生烦恼、断灭生死轮回,是要教会人类如何脱离烦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劝人积极面对生命中一切现象。佛教可以为人类提供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撑。其实这对于处于高压状态的现代人来说,不啻为一副良药。当这种供给与需求相结合,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即人们对于佛教思想有极大的认同,工作和生活之余会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佛教概念,比如中国的一些成语、俗语、传统节日等。所以,现代佛教的世俗化也就意味着生活化,意味着现代化,意味着以更强的普世性渗透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进程,也就成了佛教现代化的趋势和反映,其突出反映就是佛教通过慈善公益事业越来越明显地体现着自身存在的价值。
综上所述,在某种意义上,世俗化亦意味着现代化。即通过入世行为在现实世界架构其神圣天堂,建立适于现实需要又促进自身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的轨制,客观上重新确立其在世俗各层面之绝对位置。
在佛教世俗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与其它宗教如基督教相比,在传教方式上有着很大差别,基督教相对自由、形式灵活,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佛教,但很多被一些邪教所利用,成为掩人耳目的工具,这值得佛教在世俗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反思,寻求一种有效机制确保佛教的健康发展。
注释:
[1]《太虚全书》精装本第29册,第77页。台湾善导寺佛经流通处印行,1998年。
[2]江灿腾:《当代台湾人间佛教思想家》,第5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版。
[3]请参阅濮文起:《人间佛教理念的发展历程》,《中国宗教》2006年02期57页。
[4]印顺法师:《华雨集(五)》,第99-101页,台湾正闻出版社: 1993年版。
[5]请参阅星云法师:一九九O年元旦《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的演讲。
参考文献:
[1] 《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太虚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3] 印顺:《佛在人间》,《妙云集》[M].正闻出版社1981年版。
[4] 《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印顺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
[6]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7]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连放生护生会[8] 石峻,楼宇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2册》[M].中华书局,1983年1月版。
[9] 张志刚,宗教研究指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陈士强教授:玄奘生平史料七种综述陈士强教授:玄奘生平史料七种综述
陈士强
今存的记叙玄奘生平事迹的资料主要有七种:一、唐玄奘口述、辩机笔受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二、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玄奘传》;三、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丫,四、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卷四《玄奘传丫,五、唐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六、唐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一卷;七、唐佚名《口口寺沙门玄奘上表记》一卷。这些资料的记叙各有侧重,而且并非全然一致,今据笔者所阅,作一粗略的介绍,以供有志者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一、《大唐西域记》。据唐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唐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玄奘费经像回到长安,随后前往洛阳,谒见唐太宗。唐太宗仔细地向他询问了西行路上的所见听闻,“并博望之所不传,班(班固)马(司马迁)无得而载一,太宗对此很感兴趣,因而对他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敦,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一玄奘回到长安以后,一边组建译场,创译《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敦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等等一批梵文佛经(凡五部五十八卷),一边由他自己口述、弟子辩机笔受,撰《大唐西域记》,贞观二十年(646)七月撰成进呈。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发自高昌,杖钖西行,周游印度各地,参学巡礼,最后费经回国的漫长旅程中,所经行的百一拾个国家和听闻所得的廿八个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国家的名称、方位、疆域、地形、城廓、居室、种族、刑政、兵制、赋税、货币、言语、文字、教育、岁时、衣饰、馊食、礼仪、风习、气候、田畜、物产,以及名胜古迹、人物传说、历史掌故、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信仰)等。此书大体上是按玄奘取经时经行的路线记述的,但在经行国家的先后顺序上,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据《西域记》卷一的记载,玄奘到了羯霜那国之后,即去缚暍国(缚暍国之前记叙的睹货逻国故地因是听闻国,故不在经行的路线之内)。而据《慈恩传》卷二的记载,玄奘到羯霜那国之后,先去活国,再去缚暍国。《西域记》卷十在奔那伐弹那国之后,所记叙的国家依次是:迦摩缕波国——三摩咀吒国及以东六国(听闻国)——耽摩栗底国——羯罗孥苏伐刺那国——乌茶国。而《慈恩传》卷四则为:羯罗孥苏伐剌那国——三摩咀吒国及以东六国(听闻国)——耽摩栗底国——僧伽罗国(听闻国)——乌茶园,没有迦摩缕波国,而且是先到羯罗孥苏伐刺那国,再到耽摩栗底国,而不是相反:至于《西域记》卷十一记载的从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到伐刺孥国,沿途经行的国家,与《慈恩传》卷四、卷五所记,更是大相径庭。
二、《大唐内典录·玄奘传》。此传作于唐麟德元年S64),作者道宣是玄奘的弟子,曾参与佛经的翻译。由于《大唐内典录》的体裁是佛经目录,故作者在记叙玄奘的生平事迹时,主要记叙的是他翻译的佛经的名目部卷,但统计不全,连同《大唐西域记》在内,只有二八十七部一千三百四十四卷一。
三、《续高僧传·玄奘传》。此传作于唐麟德二年S65),《西域记》只记玄奘西行取经及回归时所经行或听闻的西域国家。而此传则前记玄奘的生世、出家、求学、行化,中记玄奘的西域行程,末记玄奘归国以后的译经活动,首尾完整,其资料既有取于《西域记》的,也有取于玄奘的表状的,还有根据玄奘平时的讲述加进去的。书中所记玄奘翻译的经论名目,“总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虽未列出具体的经名,但其总数显然较《内典录》有了增加,从而表明作者已对《内典录》的记载作了多正。
四、《古今译经图纪·玄奘传》。《古今译经图纪》约作于麟德二年S64)信当时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为纪念玄奘的译经功绩,在墙上画了历代佛经翻译家的图像,始自东汉的迦叶摩腾,终于唐代的玄奘。作者靖迈既为玄奘的弟子,便受命为每幅图像配写了人物小传。但由于这些人物小传属题记性质,故对人物的生平行历着墨不多,而对他们的译典则二具列。传中所录的玄奘译经数目,“除《西域记》,总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个数目较为准确,因而为后代的佛经目录如唐智升《开元释敦录》等所采纳。
五、《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名《丈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藏法师传》、《慈恩传》,十卷。唐麟德元年(664),魏国西寺沙门慧立初撰:垂拱四年(688),弘福寺沙门彦惊续成。故书题“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惊笺”。慧立,与前面提到的辩机、道宣、靖迈,以及栖玄、明璇、行友,道卓、玄则共为玄奘译场的“缀文大德”,参预译经积十九年之久。故彦惊《序》说:“(慧立)睹三藏(指玄奘)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赞之仰之,弥坚弥远,因修撰其事,以贻终古。及削稿云毕,虐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闻。尔后役思缠疴,气悬钟漏,及顾命门徒掘以启之,将出而卒。”也就是说,早在玄奘在世的时候,慧立已在私下编录玄奘的事迹,至玄奘去世时已勒成初稿。由于担心所记或有不周之处,会引起同门长幼的非议,故将书稿包起来,埋藏于地下,一直到自己身患重病,奄奄一息时,才向自己的门徒交代,叫他们将书稿挖出来,遗憾的是,书稿还未挖出,慧立便绝气身亡。取出后的书稿经众人传阅,逐渐流散,相隔了奸几年,才有门人搜集齐全。由于慧立的稿本主要记述的是玄奘的身世、出家前后的经历以及西域之行,没有记述玄奘回国以后的译经活动,故慧立的门人祈请彦惊作序,并加以赓续,于是始有今本《慈恩传》。
今本《慈恩传》的前五卷是慧立写的,不过所记当以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春正月从西域回到长安为止(即第六卷起首“释彦惊述曰”之前的文字),但在文字上已经彦惊修改:后五卷基本上是彦惊新撰的,不过卷十之末所载的慧立的;姗赞二对全书内容的总的评论),原先当在慧立初撰的五卷本的末尾,是彦惊在补续时将它们栘至卷十之末的。
《慈恩传》与《西域记》在内容上有一定的联系。《慈恩传》在撰作时曾参阅过《西域记》,并采用了《西域记》中对西域各国名称的新译,以及部分资料。《慈恩传》卷四在记述僧伽罗国和摩腊婆国时两次出现“语在《西域记》”的说法,便是其中的一个证据。但《慈恩传》关于玄奘西域之行的叙录,并不是根据《西域记》改编而成的,而是直接借助于慧立从玄奘的讲叙中所获得的资料编纂起来的。因为《慈恩传》中虽然也有玄奘亲践或听闻的西域各国的山川地理、风物人情、宗教信仰、佛教名胜遗迹,以及历史传说等等的记载,对勘后,可知是参考《西域记》而扼述的。但它的重点不是记国(《西域记》卷一、卷三、卷四、卷七、卷十凡有十二国未见于《慈恩传》),而是记人,即玄奘的行事,诸如玄奘在哪一国,遇到过甚么人和甚么事,瞻仰过何处圣迹,求学过哪位大师,以及其他活动,而这些情况,大半为《西域记》所不载。而且有关玄奘的行径次第和路线也叙述得更为清晰。有些记载也与《西域记》下同,关于这一点已在前面提及了。
但《慈恩传》也有不足之处。如对玄奘的生卒年缺乏前后一致的记载。
若据卷一“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具足戒)”的说法,则玄美生于仁寿三年S03):若据同卷玄奘在贞观三年出发西行,“时年二十六”的说法,则玄奘生于仁寿四年(604):若据卷十玄奘在龙朔三年(663)对诸僧说的“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指玉华宫,又称‘玉华寺’),则玄奘生于开皇十九年(599)箱生年既不一致,卒时的岁数自然也难以确定。这种情况虽然也存在于《续高僧传·玄奘传》之中,但它中间有一说倒是可以肯定的,即“麟德元年,(玄奘)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于玉华。”此话的意思与《慈恩传》所记大致相同,但时间上有出入。相比之下,《续高僧传·玄奘传》将说话的时间定为玄奘去世的当年,即麟德元年(664)较为合理。据此,玄奘的生年应是开皇二十年(600),卒时六十五岁。另外,据《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玄奘曾奉唐太宗之命,将《老子》译成梵文,传之西域。又将《大乘起信论》从汉文还译为梵文,使之流布天竺。此二事,《慈恩传》也脱漏未载。
六、《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这篇《行状》的作者冥祥是唐高宗时人,曾参加过玄奘的葬礼,但他与玄奘之间没有师徒关系。《行状》全文约一万一千字,比《续高僧传·玄奘传》少七千字左右。通过对勘发现,《行状》实是以《慈恩传》十卷本为底本改写而成的,因而可以确定为是垂拱四年(688)以后写的。《行状》虽然本于《慈恩传》,但叙述简洁明了,易于阅读。有些地方糅入了《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记载,以及冥祥个人的新提法。如说玄奘在东都净土道场为师复述,“时年十五一:武德五年,玄奘“年二十有一”;贞观三年,“时年二十九一等,均是以《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说法而取代《慈恩传》之说的。至于玄奘在蜀地“四五年间,究通诸部”的“四五年间一,则是冥祥的新说。另外,《行状》中也引用了玄奘临终前说的话:“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华”中的二八十有三”疑是二八十有五”之误。
七、《口口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略称《玄奘上表记》。此书今存的原本为日本小泉策太郎收藏的唐代手钞本,在我国已经失传。书首脱落两个字,从书中收载的最后一篇奏表(《请御制大般若经序表》所署的“龙朔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坊州宣(宜)君悬(县)玉华寺沙门上表”等句来看,脱落的当是“玉华”两字,故它的全称当是《玉华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由于书中所载的表启与敕答的名称,凡涉及李世民的,一般称“太宗文皇帝一,而涉及李治的则直称“皇帝”,而不称庙号二局宗一。以此推断,编集的时间大致上在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去世以后不久,编集者很可能是玄奘的弟子。此书共收录表敕四十一篇,其中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十一篇,在高宗朝的上表二十三篇,太宗的敕书四篇,高宗的敕书三篇(内有诗一首)。
《玄奘上表记》的前部分,即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和唐太宗的敕答,与一部题名为《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一卷)的书相同。《表启》是日本奈良时代写的京都知恩院藏本,《玄奘上表记》与之相异的有两点:一《表启》的首篇是贞观二十年七月十三日的《进经论等表》,而《玄奘上表记》则缺此篇;二、《表启》所收的各篇表启都署有贞观某年某月某日上表的具体日期,而《玄奘上表记》则无。今本《玄奘上表记》(指《大正藏》收录之本)将《表启》中的《进经论等表》补入,作为首篇,而将《上表记》原先的首篇《进西域记表》改列为第二。这样,人们通常见到的《大正藏》中收录的《玄奘上表记》实收表诏是四十三篇。
《玄奘上表记》对于研究玄奘从印度学成回国后的主要活动,特别是自贞观二十二年(646)至龙朔三年(663)的十八年间的译经、交往以及晚年的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其中有些表启的内容与《慈恩传》叙录不一,可资参比。有些表启则为《玄奘上表记》独家所有,可补《慈恩传》之阙遗。如《玄奘上表记》所收的《进经论等表》,也见载于《慈恩传》。但两书所载的同一篇表章,除新译的五部经论的名目卷数是一致的以外,其余的前言后语全异,即是其中的一例。然而,由于《玄奘上表记》在编集时省略了各篇表启的上表时间(最后一篇除外),故它又必须借助于《慈恩传》等的记载,方能考定时间。另外,它只是收录了玄奘上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除上述七种有关玄奘生平事迹的史料以外,记载玄奘译经名目的,还有唐代静泰于麟德二年(665)编的《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所记与《古今译经图纪·玄奘传》相同,也是“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稍晚的还有唐代刘轲撰的《塔铭》。
原载《内明》第274
- 内蒙放生团,放生蚯蚓999
- 广州买活鱼放生,广州放998
- 西安放生团,放生时念998
- 今日宜放生吗莆田代放997
- 放生乌龟的精美句子997
- 放生要放什么佛乐,放997
- 水库适合放生什么动物997
- 为已故的人放生流程996
- 江苏黄鳝去哪里放生,996
- 能替别人放生吗有讲究996